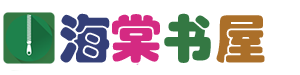第409章 齐地一猪倌
“仓颉作书~以教后嗣~
幼子承诏~谨慎敬戒~
…
勉力讽诵~昼夜勿置~
敬务成史~计会辩治~~~”
天子荣新元二年,齐都临淄。
旭日东升。
一处幽静的院落内,不时传出稚童们咿咿呀呀的诵读声。
孩童们或身着华服,或衣衫褴褛,却无不在书案前正襟危坐;
儒冠老生们佝偻着腰,将戒尺背握于身后,微眯着眼,一边在学堂内巡视,一边侧耳倾听孩童们诵读的内容。
学堂外,年龄稍大些,约莫十岁出头的孩子们,则一边在心中跟着默念这个时代的启蒙读物——《仓颉篇》,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。
有人在劈柴;
有人在担水;
甚至还有几人撸起袖子,一边在灶台前忙着煮饭,一边在心中默默背诵:君子远庖厨……
整个院子由内而外,都散发着极为浓厚的儒学气息。
当然,不是后世那些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,四肢不勤、五谷不分的那种‘儒学’;
而是战国遗风极为浓厚的、独属于这个时代的‘特色儒学’。
——后院的空地上,二十来岁的年轻人‘闻鸡起舞’,正顶着儒冠武剑!
院外不远处的山丘上,更有几人于树荫下抚琴而歌,研习音律。
如此景象,在缓缓升空的朝阳照耀下,尽透出一阵令人心绪舒畅的欣欣向荣之景象。
只不过,在明显更为僻静的侧院,气氛却莫名有些阴沉。
老树根下,一儒冠老者躺靠在最近几年,才刚在长安流行起来的躺椅之上;
老者眉头微皱,单手持卷,只是心思,却显然不在手中书卷之上。
躺椅前三两步的位置,一位稍年轻些,却也同样发鬓斑白、头顶儒冠的老者,此刻却毕恭毕敬的持子侄礼,满目哀求的对躺椅跪地叩首。
就好像是后生晚辈,祈求父祖答应自己的某个请求;
只是这个后生晚辈,也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……
“自秦亡而汉兴,我儒家之学,便多为天下人所不耻。”
“——尤其当年,太祖高皇帝宁拜叔孙通为礼官,也不愿重用我儒家正统:鲁儒一脉时起,我儒家,便几可谓寸步难行。”
“更别提那‘高阳酒徒’之类的逸闻趣事,又或是太祖高皇帝,动不动拿我儒家士子寻乐,更甚是折辱……”
漫长的沉默,终还是被躺椅上的老学究所打破。
只是嘴上虽说着话,老学究的目光,却依旧锁定在手中竹简之上。
一番话说出口,又顶着手中书卷看了许久,老学究才悠然发出一声长叹。
旋即将手中竹简丢在腿上,缓缓侧过头。
“次卿,当真打定主意了吗?”
“当真要为那‘科考’二字,而走这一趟长安?”
次卿,是那跪地男子的表字。
男子姓公孙,单名一个‘弘’字。
至于躺椅上的男子,正是这齐郡,乃至天下闻名的儒学大家:胡子都——胡毋生。
先帝年间,胡毋生与同门师兄弟——同习《春秋公羊传》的董仲舒,在长安担任博士。
后来年纪大了,又觉得留在长安没什么意思,胡毋生才告老还乡,回了临淄教书育人。
——说来,胡毋生此刻正坐着的躺椅,都还是先帝所赏赐!
至于先帝从何得来如此妙物,那就没人知道了……
“回老师的话。”
“学生,有心一试。”
胡毋生一番询问,公孙弘也总算是开了口,表达了自己的意愿。
见老师胡毋生仍不为所动,依旧是一副有心再劝,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迟疑之色,公孙弘不由苦笑着摇摇头,又莫名发出一声哀叹。
“学生这一生,老师是再清楚不过的。”
“年少时,蒙父荫为狱吏,不数岁,为宵小所迫害,因罪免官。”
“后治《诗》《书》,年不过二十,便因才能闻于郡县。”
“——说来,那贾谊贾长沙,也是和学生一个年纪。”
“太宗皇帝拜贾长沙为博士时,学生也同样是在二十岁的年纪、同样被太宗皇帝拜为博士。”
…
“学生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:在当时,人人都说汉家,一连出了两个二十岁的小博士。”
“可从不曾有人在意:这两位小博士当中,除贾谊之外的另一人是谁……”
说着说着,公孙弘略显老迈的面容之上,也不由涌现出阵阵落寞之色。
又一声哀叹发出,便闻公孙弘继续说道:“贾谊之才,学生自愧不如。”
“说不嫉羡,那是假话;”
“但即便稍有嫉羡,也不过是望其项背,而以自强罢了……”
…
“学生自知不如贾谊远矣,所以在四十岁的年纪,毅然决然丢下了从二十岁起,就一直在担任的博士一职。”
“——学生,不是不愿留在长安;”
“而是学生不愿在长安,做一个不为人知、不为人敬,甚至没人知道公孙弘是谁的所谓‘博士’。”
“故而,学生还乡,再治《春秋公羊传》,厚颜无耻的自诩为‘胡生胡子都之门徒’,以这样卑劣的方式,拜入老师门下。”
“虽然只接受老师的教导不过数年,远不至‘登峰造极’之地步,但也终归是学有所成——至少是略有所成。”
“若非此番,长安传回科考之信,学生或许会一直在临淄,接受老师的指导,甚至终生都未必会再回长安。”
“但……”
说到最后,公孙弘不由自主的低下了头,只如倔强的少年般轻轻攥紧拳头,面上也悄然涌上些许不甘。
——二十岁,被汉太宗孝文皇帝拜为诗博士,与同样年纪的贾谊贾长沙并列!
这,是公孙弘这一生当中,最高光的时刻;
同时,也是公孙弘毕生难忘,且至今都满怀不甘的过往。
凭什么?
凭什么他贾谊,就能集天下人之关注,而公孙弘,就只能做个没有半点存在感的陪衬?
甚至别说是陪衬了——问问现如今,还活跃在长安朝堂的老臣,有谁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长安,有一个和贾谊同岁,且同样被拜为博士的少年?
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说‘我记得’。即便偶有人说:哦~是了,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,当年除了贾谊,好像是有另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,也一并被拜为博士。
但公孙弘很确定:如今长安,绝不可能有哪怕一个人,记得那个同样二十岁的小博士,是齐人公孙弘……
正如公孙弘方才所言:对于贾谊的才华,公孙弘自愧不如。
甚至可以说,在二十岁的年纪,担任太宗皇帝的博士后,那长达二十年的博士生涯,公孙弘的绝大部分精力,都放在了学习、深造,追赶贾谊之上。
只是贾谊抑郁而终,公孙弘失去了努力方向;
再者,公孙弘也逐渐发现:在长安,在那帝都繁华之地,自己根本无法静下心来,专心搞学问。
于是,公孙弘顶着整个世界不解的目光,毅然决然丢弃了什么都不用做,每年就能有一千八百石俸禄的博士职务,来到了临淄。
回想起年少时,那段艰苦的岁月——无论是在祖籍薛县做狱吏,被那些老油子同时欺负,甚至最终被陷害丢了官职;
还是后来,失去生活来源后,自己只能一边牧猪,一边苦学《诗》《书》。
至今为止,菑川郡薛县的老者们,都还有人记得曾有一个叫公孙弘的年轻人,在为富户牧猪时,腰间总是别着一卷又一卷竹简。
还有人记得那个叫公孙弘的年轻人,总是因为看书太过投入,而让猪跑丢,隔三差五就要吃东家的挂落。
那般艰难的二十年过后,又是看似体面,实则无比空虚的二十年;
时至今日,公孙弘已经五十又二,却依旧在潜心治学,以图‘更上一层楼’。
虽然不知道如今的自己,距离曾经惊艳天下的贾长沙还有多远,但公孙弘却依旧不敢有半点松懈。
如果不出意外,公孙弘的一生,原本就是这样了。
——五十多岁的年纪都还在‘学习’,指不定哪天,就学着学着老死了;
就算长寿些,等学有所成,才华被长安朝堂看到,公孙弘也早就是个垂垂老矣、行将就木的老人了。
可这意外,偏偏就出了。
轻飘飘‘科举’二字,便让原本心如止水的公孙弘,那早已被长安伤透、早已被贾长沙打击的体无完肤的心,重新泛起了层层涟漪……
“既是有了决断,直去便是。”
“何以此番,叩首请辞?”
公孙弘一番真情流露,胡毋生便大致明白:眼前这个并不比自己年幼多少的‘学生’,大概率是听不进去劝了。
于是顺势搭了个台阶,便见公孙弘就势接道:“学生厚颜,欲请老师修书一封。”
“——学生虽于长安为博士二十余载,怎奈除贾生一人,便再不曾有过故旧、至交。”
“若老师愿修书一封,请董师叔收留学生一段时日,学生,感激不尽……”
公孙弘口中的‘董师叔’,自然是当年和胡毋生一同被先帝拜为博士,却并没有和胡毋生一同还乡,而是至今都还在长安的《春秋》博士:董仲舒。
对于公孙弘‘在长安没什么认识的人,没地儿落脚’的解释,胡毋生是一万个不信。
但胡毋生也清楚:弟子公孙弘想要的,并不是一个落脚之地,而是一个能在长安,为自己指明道路、趋利避害的人。
很显然,胡毋生在长安的人脉关系当中,最能拿得出手、最能帮到公孙弘的,便是博士董仲舒。
只是公孙弘再怎么厚颜无耻,也终归没好意思直说‘请老师找个人帮我’,这才委婉的说:去了长安没地儿落脚,不知道能不能住董师叔那里……
“博士有多难做,我也不是不明白。”
“——守得住清贫,耐得住寂寞;”
“说来轻松,可真要是做,又谈何容易?”
“所以,次卿辞官返乡,我向来都不曾说次卿‘不智’。”
“因为我自己,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,辞官回临淄治学的。”
如是一番话,表达了自己对公孙弘‘辞官深造’的赞同,胡毋生又是一阵默然沉吟。
过了许久,才再度长叹一气,重新拿起竹简,再度恢复到先前一边看书,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说话的模样。
“我在长安虽不过数年,却也是有些熟人。”
“这所谓‘科举’,我也得了些消息。”
“——三轮文考,即便全部通过,也不过是四百石的佐吏起步;”
“次卿,可是曾辞去二千石博士的职务,回到临淄治学的啊……”
“治学十数年,再回长安,去和后生晚辈以文竞之,最终,却只做个四百石的小吏?”
“次卿,当真有此愿?”
胡毋生话音落下,公孙弘也不由陷入一阵沉思之中。
关于自己的未来,公孙弘曾和老师胡毋生商讨过。
再潜心深造个十来年,过了六十岁,再加上有老师胡毋生的名气,公孙弘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地位,大概率就能达到‘名士’的级别。
等一个机遇,被某个达官贵族举荐——甚至只需要老师胡毋生亲自举荐,公孙弘便大概率能得到长安朝堂的征辟,举为贤良方正。
在原本的历史上,公孙弘也恰恰是在六十岁的年纪,被新君继立的汉武大帝一纸‘强制郡国二千石举贤良方正’诏,从而得以征辟入朝的。
但此刻,公孙弘却半点都不觉得:从四百石小吏做起有什么不好。
二千石又如何?
一个看似体面,实则半点权利都没有,三年五载都得不到天子召见一次的博士官,难道真就比那所谓的‘百石小吏’强?
至少在公孙弘看来,并非如此。
——四百石小吏,哪怕是个‘吏’,也终归是能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,切切实实去做点什么。
而二千石的博士,却大都穷其一生,都无法为宗庙、社稷——为天下人做哪怕一件实事。
就说眼前的胡毋生,做了五年的博士,满共就见了先帝一面,得到了一把躺椅作为赏赐;
其师弟董仲舒更惨——至今都做了快九年的博士,无论是先帝还是当今刘荣,都不曾有哪怕一次私下召见。
归根结底,公孙弘要做的,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谈阔论,随遇而安的纯知识分子。
公孙弘的目标,是贾谊贾长沙!
即便无法成为贾谊那样绝艳千古的人物,公孙弘也要竭尽所能,在华夏的历史篇章中,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风姿。
“学生,确有此愿!”
这个回答,公孙弘给的务必坚决。
片刻之后,一封早已写好的‘介绍信’,也被胡毋生从怀里掏出,头也不抬的递到了公孙弘面前。
“去了长安,先去拜访魏其侯窦婴。”
“魏其侯于我,也算是有些渊源。”
“——且去~”
“若事不可为,大可再归临淄;”
“我师徒二人,仍可有教无类,为我儒学开枝散叶……”
(本章完)
第409章 齐地一猪倌
同类推荐:
临高启明、
穷鬼的上下两千年、
弃狗(强制1v1)、
进入恋爱循环以后(NP)、
大隋风云、
黑网行动、
最强雇佣军、
漫威里的灵能百分百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