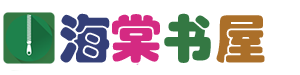第410章 八方英才聚长安
公孙弘,是幸运的。
曾为太宗皇帝博士的履历,以及师门提供的人脉,让公孙弘此行长安,多了不止三两分底气。
但公孙弘这样的幸运儿,终归还是少数。
更多的,还是一没有政治履历,二在长安没有人脉——甚至到了长安都不知道住在哪里、吃在哪里的‘普罗大众’。
和真正的普罗大众,也就是占据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底层农户相比,他们或许还算幸运。
他们或许家底不算丰厚,但至少让他们或专心致志,或忙中偷闲,得到了知识的灌溉。
在家乡,他们或许是十里八想的俊后生,又或是文明郡县的‘青年俊杰’;
往大了说,郡县府衙的官老爷们敬他们,地方豪强富户舔他们,不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,也至少是不愁生计的一方人物。
往小了说,帮乡里乡亲写写信、读读信,又或是帮商贾算账,乃至于为贵族整理文档——总归是比在土里刨食的农人要体面不少。
但来了长安之后,一切,就都不一样了。
——后世人常说,在一朝都城,随便砸一块搬砖下去,都能砸到三五个官儿;
一条街从这头走到那头,说不定能偶遇小半个朝堂!
虽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,但事实上,长安的人口密集度和人才质量,也确实远非地方郡县——尤其是关东郡国所能比。
好比在齐地,除了王宫里的宗亲诸侯,以及城内的几家大户,就基本没什么完全得罪不起的人。
在临淄城的路上被人撞了,你只需要上下打量一下,确定对方身上穿的不是什么特别华贵的服饰,且对方没有百十仆从跟随;
然后,你就可以和对方好生理论一番,来判定一下此次‘交通事件’,究竟是谁全责了。
但在长安,一切都好似天地翻转——完全倒了个个儿!
在长安街头,平均每五个行人当中,或许都未必能挑出三个普通人!
绝大多数情况下,长安街头平均每五个行人当中,会有一名职务或高或低的官员,一名身份或尊或卑的功侯贵戚/贵族仆从,以及一名家底殷实,人脉颇广的地头蛇。
即便是剩下两个‘普通人’,看上去一副老农打扮,可你但凡惹上他,你就能知道什么叫天子脚下、什么叫帝都皇城了。
什么开国元勋、英烈之后啊~
什么落魄贵族、衰败王门啊~
亦或如今是老农的身份,实则却掌握着不亚于官员、贵族的权利,人脉能直达庙堂的神秘老者——都有可能在长安街头出现。
所以,在帝都长安,你如果同人起了争执,性价比最高的选择,其实就是立马道歉。
因为你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,究竟是某个cos老农的公子哥,还是心血来潮,走上街头体验生活的公卿子弟。
反之,你的底细,光从你那一口明显异类的他乡口音,就被对方给看的偷偷地了……
所以,当时间逐渐来到秋八月,刘荣意料之中的‘长安治安状况面临挑战’的情况,竟出人意料的没有发生。
前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,关中地区的考生,便基本已经悉数抵达长安。
即便是关东,路途稍微近一点的——如梁地、淮泗地区,以及汉中、巴蜀,乃至北地、陇右的考生,也都先后抵达长安。
然后,他们极其本分的,找到了自己该落脚的地方。
——有亲人的寻亲人收留,有故交的找故交拜访;
实在是头一回来长安,也根本没什么人脉的,也都按照各自的经济状况,规规矩矩找了临时落脚点。
手头殷实点的,就在长安租,乃至直接买下一栋民居;
差一点的,要么几人合伙租下一栋小院,又或是直接找到客栈,低价要一个只可容纳一人的大通铺床位。
倒是长安城的街头,在秋收都还没到来的眼下,就先一步热闹了起来。
有钱的公子哥们走上街头,这儿逛逛、那儿看看,累了就在酒肆与友人喝几杯;
囊中羞涩的穷酸们,也没有把自己锁在房间看书——有经济压力的就去找个活计,或帮人抄书、算账,或帮人搬运货物;
即便是没有经济压力的,也同样本着‘读万卷书,不如行万里路’的原则,到处结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,以求能互相学习、精进学术。
当然,也免不得有些心术不正的人,在科考还有十数日的当下,就将一篇篇辞藻堆彻,却又言之无物的所谓‘文章’,塞进朝中重臣、公卿贵戚的门。
期望得到举荐,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;
更多的,是希望自己能得到某位大人物赏识,从而帮助自己在科考走得更远也好,亦或是在科考之后,留自己在长安做点什么也罢。
言而总之,总而言之,每一个人,都在为自己的今天,以及未来而奔波。
而在这前所未有的年轻知识分子大聚集、百家思想大碰撞当中,自然就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火……
“某家,郑当时!”
长安北城,东市外的一件酒肆,青年文士齐聚。
虽非某人作主邀宴,但文士们却还是自发的聚在了一起,算是彼此打个照面、混个眼熟。
见大家伙儿都扭扭捏捏,只同身旁人交谈,却根本不理会他人,郑当时当即站起了身,简单做了番自我介绍。
“家祖郑君郑老大人,曾为楚将!”
“后项王败亡,家祖降汉,因不从太祖高皇帝‘直呼项王名讳’之令,而贬斥还乡。”
如是丢下两句话,郑当时便转动着魁梧伟岸的身躯,对酒肆内的众文士环一拱手,旋即便自顾自坐下身来。
待郑当时佯装镇定的抓起酒酬,小口抿起浊酒,酒肆内,才开始想起一阵此起彼伏的惊叹声。
“嘶~”
“郑当时……”
“梁楚豪侠郑当时!”
…
“想当年,吴楚七国之乱,张氏兄弟——楚相张尚死战,梁将张羽死战!”
“而梁中尉张羽,就曾受过郑当时恩惠,从其言而解其危!”
接连响起的两声惊呼,让众人纷纷挺直腰杆,目光也齐齐落在郑当时那看似淡定,实则早已暗暗得意的臭屁面容。
——如果仅仅是一个‘梁楚豪侠’的身份,以及一个‘先祖曾为楚将’的家族过往,那在场众人,大概率依旧不会认识郑当时是谁。即便是认识,也只会为之不齿、不屑与之为伍;
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向郑当时投去崇拜、嫉妒,却又略带些疑惑地目光。
在场众人,不说是人均家世显赫,却也至少是人均略有贤名。
至少都是有点学识、本事在身上,且以‘仕汉’为目标多年的精英知识分子。
对于这些人而言,郑当时这个人名最耀眼的身份,是当今刘荣曾经的太子舍人!
没错;
先祖曾追随项羽,且在汉家建立后,不愿直呼项羽名讳为‘项籍’,自身又是上不得台面的‘游侠’出身的郑当时,曾在先帝年间,被任命为当时的监国太子刘荣的太子舍人。
所谓太子舍人,便是太子宫属官、储君班底中,最常见的一个职务。
除了太子詹事(家令)、中车属令(下一代宦者令)、中盾卫(亲卫统领)外,绝大多数太子班底,最初都是太子舍人的职务。
照理来说,曾经的监国太子,当下已经贵为天子,郑当时这个曾经的太子舍人,也应该像无数的前辈——如先帝的太子舍人张欧、周仁等,成为当今刘荣信重的肱骨心腹。
而现在,郑当时却出现在了这里;
出现在了这处除小厮外,几乎尽由科考士子塞满的酒肆当中。
这意味着曾经的梁楚豪侠、当今刘荣太子时期的班底羽翼,也同样打算参加今年的科举。
没人知道这是为何。
没人知道郑当时,这是脑子瓦特了,还是在当今刘荣那里失了恩宠,亦或是在太子宫残酷的竞争当中被淘汰。
但大家能立刻确定的是:本次科考,有一个曾在当今刘荣身边伺候,对当今刘荣有相当程度的了解,且曾经正儿八经在长安做过官的人!
且不论这个人现在混得怎么样、怎么就沦落到要科考的境地——单就是这个人的来历,就足以让众人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!
“郑当时……”
“郑当时………”
人群中,立时便有几人不着痕迹的低下头,在心中牢牢记住了这个人名。
——梁楚豪侠、故太子舍人郑当时!
本次科考的第一大热门,或者说是焦点人物,也随之浮出水面。
“鄙人,主父偃(yǎn),齐郡临淄人氏……”
郑当时之后,又站起来一名身材消瘦,眉宇略带阴戾的男子;
只是考虑再三之后,主父偃终还是按捺下介绍师承、学说的想法。
——长短纵横术!
这个学说在这个时代有多异类、有多不受待见,主父偃从小到大,已经体会了无数次。
简单的姓名、籍贯,再加上主父偃本身就没什么知名度,以及像样的履历,大家伙便也没太关注主父偃;
只礼貌性的露出一个微笑,旋即便将目光投向了第三人。
“鄙人,倪(ni)宽,籍齐地千乘郡。”
“少治五经,后受欧阳生——欧阳和伯授《尚书》。”
这第三人的自我介绍,倒是比先前的主父偃,引得了更多的关注。
一来,倪宽这番自我介绍,算是委婉的透露了自己的学派——儒家。
二来,倪宽治的又是儒家诸学中,相对比较罕见,且含金量又较高的《尚书》。
——想当年,晁错得以一飞冲天,于太宗皇帝年间,跻身先孝景皇帝的太子宫,便是凭着《尚书》博士的身份。
可以说,在儒家六经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当中,《乐经》已经失传的当下,余下五者,含金量最低的就是《诗》。
不是《诗》不值得学,又或是‘言之无物’,没有学习价值;
而是如今天下治《诗》的人太多,乃至于都按照地域,分出齐诗、楚诗等不同流派了。
这就导致天下,无论是儒家士子还是黄老、法、墨,亦或是儒家内部其他流派——几乎人人都治《诗》。
这就好比后世,大学生的专业千千万,但思政和马列,都是默认都要学的必修科目。
《诗》,就是这个时代所有文人士子的思政必修课。
含金量比《诗》稍微高一点的,是至今都还被鲁儒垄断的《礼》。
《礼》的地位低,除了其内容高高在上、不够务实,以及鲁儒这个群体的减分外,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:《礼》在这个时代的全称,并非后世人更耳熟的《礼记》,而是——《周礼》。
周的礼法。
如今都是汉室了,周的礼法又怎么可能得到重视?
尤其如今汉室,更是早自太祖高皇帝之时,就被天下人公认——乃至太祖刘邦本人都承认的‘礼崩乐坏’的时代。
既然都礼崩乐坏了,那周礼,自然是有用的时候翻出来看看,没用的时候就丢在一边了。
再考虑到《礼》的正统,或者说是解释权,至今都还被令人恶心的鲁儒一脉所垄断,就更导致了《礼》学的落寞。
《诗》最烂大街,《礼》最不受待见,再往上,则是《易》。
准确的说,是《周易》。
虽然和《周礼》一样,都占了个‘周’字,但《易》的学术地位,实际上是儒家六经当中最高的!
至于综合含金量排序,《易》之所以排在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之后,也绝非《易》比不上后者;
而是相较于《尚书》《春秋》,《易》实在是太过于晦涩难懂,愿意学的人太少,能教明白的人更少。
所以,绝大多数情况下,儒家出身的士子,无论是在儒家内部的鄙视链,还是外部的‘食物链当中’,都是以治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者,作为最具含金量的头部。
至于《易》?
但凡能说出个一二三四,直接就是当世大家!
只可惜这样的人,自有汉以来,都不超过五指之数,且从不曾有两个人同时处于学术鼎盛期。
(本章完)
第410章 八方英才聚长安
同类推荐:
临高启明、
穷鬼的上下两千年、
弃狗(强制1v1)、
进入恋爱循环以后(NP)、
大隋风云、
黑网行动、
最强雇佣军、
漫威里的灵能百分百、